 1359 人氣
1359 人氣
2005年,原勞動(dòng)和社會(huì)保障部發(fā)布《關(guān)于確立勞動(dòng)關(guān)系有關(guān)事項(xiàng)的通知》(勞社部發(fā)〔2005〕12號(hào))的第一條“一錘定音”,確定了司法實(shí)踐中長(zhǎng)期以來(lái)普遍遵循和適用的認(rèn)定(事實(shí))勞動(dòng)關(guān)系的標(biāo)準(zhǔn),其中包含了三方面的構(gòu)成要件:
1、主體適格——用人單位和勞動(dòng)者均須符合法律、法規(guī)規(guī)定的主體資格。
2、當(dāng)事人之間存在人身從屬性和經(jīng)濟(jì)從屬性——用人單位依法制定的各項(xiàng)勞動(dòng)規(guī)章制度適用于勞動(dòng)者,勞動(dòng)者受用人單位的勞動(dòng)管理,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有報(bào)酬的勞動(dòng)。
3、當(dāng)事人之間存在組織從屬性——勞動(dòng)者提供的勞動(dòng)是用人單位業(yè)務(wù)的組成部分。

如果要問(wèn)在校學(xué)生、退休返聘人員、外國(guó)人和港澳臺(tái)人員與中國(guó)境內(nèi)的用人單位能否建立勞動(dòng)關(guān)系,以及自然人與自然人之間能否成立勞動(dòng)關(guān)系等問(wèn)題,其實(shí)都屬于上述第一方面構(gòu)成要件的認(rèn)定范疇。
其中,對(duì)于學(xué)生工,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(gè)方面來(lái)說(shuō):
首先,未滿(mǎn)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(如小學(xué)生、初中生),肯定是不具備勞動(dòng)者的主體資格的。這類(lèi)人且不用論及其在校學(xué)生的身份,因?yàn)橹灰礉M(mǎn)十六周歲都屬于童工,而我們國(guó)家的法律是明確禁止招用童工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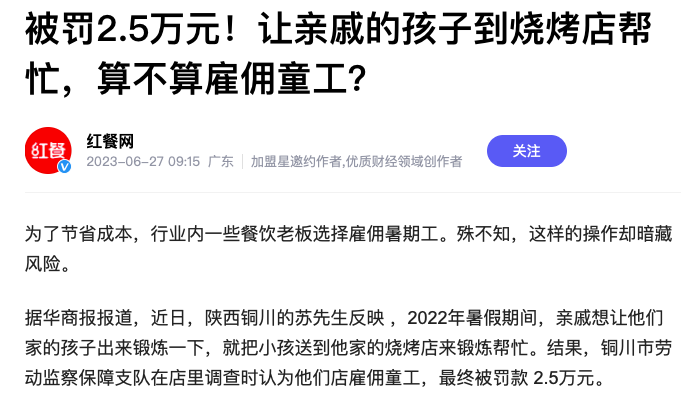
其次,已滿(mǎn)十六周歲不滿(mǎn)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稱(chēng)為未成年工。我國(guó)的法律雖然對(duì)未成年工進(jìn)行特殊的勞動(dòng)保護(hù),但卻并不禁止其就業(yè),因此,未成年工是具備勞動(dòng)者的主體資格的。
然而,雖然在年齡上已年滿(mǎn)十六周歲,但并不是說(shuō)就一定可以和用人單位建立勞動(dòng)關(guān)系,因?yàn)楦鶕?jù)原勞動(dòng)部《關(guān)于貫徹執(zhí)行<中華人民共和國(guó)勞動(dòng)法>若干問(wèn)題的意見(jiàn)》第12條“在校生利用業(yè)余時(shí)間勤工助學(xué),不視為就業(yè),未建立勞動(dòng)關(guān)系”的規(guī)定,通常來(lái)說(shuō),在校學(xué)生和用人單位之間是不能建立勞動(dòng)關(guān)系的。比如高中生、大學(xué)生,他們利用業(yè)余時(shí)間做兼職或者打暑假工、寒假工的,一般認(rèn)定和用人單位之間不成立勞動(dòng)關(guān)系,而是按勞務(wù)關(guān)系認(rèn)定。

由此,從某種程度上說(shuō),在校學(xué)生是不具備勞動(dòng)者的主體資格的。我們可以看到,在很多案例當(dāng)中,當(dāng)認(rèn)定大學(xué)生與用人單位之間是否成立勞動(dòng)關(guān)系時(shí),該大學(xué)生是否已經(jīng)畢業(yè)將作為很重要的判斷依據(jù)。
當(dāng)然,在讀的全日制大學(xué)生,在畢業(yè)前與用人單位不能建立勞動(dòng)關(guān)系,這是比較好確定的。然而,在讀的研究生與用人單位能不能建立勞動(dòng)關(guān)系,是不是也適用原勞動(dòng)部《關(guān)于貫徹執(zhí)行<中華人民共和國(guó)勞動(dòng)法>若干問(wèn)題的意見(jiàn)》第12條的規(guī)定,就不那么好認(rèn)定了!
其中一個(gè)很重要的原因是,有不少人是就業(yè)了一段時(shí)間才讀研的,有的甚至是一邊讀研,一邊還在原用人單位工作,而且可能上班時(shí)間、工作內(nèi)容和勞動(dòng)強(qiáng)度等均和之前一樣。這種情況下,當(dāng)然就不能再機(jī)械地套用原勞動(dòng)部《關(guān)于貫徹執(zhí)行<中華人民共和國(guó)勞動(dòng)法>若干問(wèn)題的意見(jiàn)》第12條的規(guī)定了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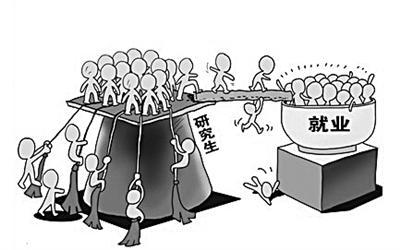
從司法實(shí)踐的情況來(lái)看:
首先,如果是就讀非全日制研究生的,一般會(huì)認(rèn)定不適用原勞動(dòng)部《關(guān)于貫徹執(zhí)行<中華人民共和國(guó)勞動(dòng)法>若干問(wèn)題的意見(jiàn)》第12條的規(guī)定,既不會(huì)認(rèn)定為利用業(yè)余時(shí)間勤工助學(xué),也不會(huì)認(rèn)定為不以就業(yè)為目的,進(jìn)而認(rèn)定該勞動(dòng)者是可以和用人單位建立勞動(dòng)關(guān)系的。相關(guān)判例為:
“對(duì)于第1項(xiàng)爭(zhēng)議焦點(diǎn),上訴人北方出版公司主張被上訴人劉恒駿系在校生,認(rèn)為在校生利用業(yè)余時(shí)間勤工助學(xué),不視為就業(yè),未建立勞動(dòng)關(guān)系,可以不簽訂勞動(dòng)合同。被上訴人劉恒駿主張其并非在校生,只是申請(qǐng)南京大學(xué)同等學(xué)歷碩士學(xué)位。一審已經(jīng)查明,被上訴人劉恒駿并非全日制研究生,其入職上訴人北方出版公司時(shí),上訴人北方出版公司要求提供入職材料,被上訴人劉恒駿提供了本科學(xué)歷。被上訴人劉恒駿在上訴人北方出版公司的工作性質(zhì)并非利用業(yè)余時(shí)間勤工助學(xué),而基本是滿(mǎn)勤工作。因此,上訴人北方出版公司關(guān)于被上訴人劉恒駿系在校生利用業(yè)余時(shí)間勤工助學(xué)、不視為就業(yè)的主張不成立。雙方建立的是勞動(dòng)法意義上的勞動(dòng)關(guān)系。”(江蘇省南京市中級(jí)人民法院(2017)蘇01民終11328號(hào)民事裁定書(shū))
其次,如果是在讀全日制研究生,則通常會(huì)適用原勞動(dòng)部《關(guān)于貫徹執(zhí)行<中華人民共和國(guó)勞動(dòng)法>若干問(wèn)題的意見(jiàn)》第12條的規(guī)定,認(rèn)定該勞動(dòng)者不以就業(yè)為目的,進(jìn)而認(rèn)定其與用人單位之間不建立勞動(dòng)關(guān)系。相關(guān)判例為:
1、“本院認(rèn)為:勞動(dòng)部關(guān)于貫徹執(zhí)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(guó)勞動(dòng)法》若干問(wèn)題的意見(jiàn)第十二條規(guī)定,在校生利用業(yè)余時(shí)間勤工助學(xué),不視為就業(yè),未建立勞動(dòng)關(guān)系,可以不簽訂勞動(dòng)合同。本案中原告閆祥青系江蘇師范大學(xué)在讀研究生,其利用業(yè)余時(shí)間在被告山東華熙博睿房地產(chǎn)營(yíng)銷(xiāo)策劃有限公司勤工助學(xué),不應(yīng)視為原告閆祥青與被告山東華熙博睿房地產(chǎn)營(yíng)銷(xiāo)策劃有限公司之間建立勞動(dòng)關(guān)系。”(山東省濟(jì)南市市中區(qū)人民法院(2014)市民初字第3219號(hào)民事判決書(shū))
2、“本院認(rèn)為:所謂勞動(dòng)關(guān)系,是指勞動(dòng)者與用人單位在勞動(dòng)過(guò)程中建立的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關(guān)系。在勞動(dòng)關(guān)系的主體中一方是符合法定條件的用人單位,另一只能是自然人,而且必須是符合勞動(dòng)年齡條件的且具有與履行勞動(dòng)合同義務(wù)相適應(yīng)的勞動(dòng)權(quán)利能力和勞動(dòng)行為能力的自然人。根據(jù)本案查明的事實(shí),原告朱少?gòu)?qiáng)入職時(shí)為在校大學(xué)生,現(xiàn)為研究生在讀,表明原告在被告處工作時(shí)并不以就業(yè)為目的,原、被告之間應(yīng)屬于勞務(wù)關(guān)系。”(浙江省義烏市人民法院(2018)浙0782民初5234號(hào)民事裁定書(shū))
最后,有法院認(rèn)為,學(xué)生身份并不當(dāng)然被限制其作為普通勞動(dòng)者與用工單位建立勞動(dòng)關(guān)系。也就是說(shuō),在校學(xué)生的身份,并不當(dāng)然就不具備勞動(dòng)法上的勞動(dòng)者的主體資格。相關(guān)判例為:
“關(guān)于黃書(shū)舟是否可以作為勞動(dòng)者的主體資格問(wèn)題。本案,黃書(shū)舟求職工作時(shí)間發(fā)生在2018年7月,屆時(shí)其已完成大學(xué)本科階段學(xué)業(yè)并畢業(yè),也已被上海海事大學(xué)錄取為研究生但尚未就讀。原、被告就黃書(shū)舟身份是否為‘在校生’發(fā)生分歧。因原勞動(dòng)部[1995]309號(hào)關(guān)于印發(fā)《關(guān)于貫徹執(zhí)行<中華人民共和國(guó)勞動(dòng)法>若干問(wèn)題的意見(jiàn)》的通知第12條規(guī)定‘在校生利用業(yè)余時(shí)間勤工助學(xué),不視為就業(yè),未建立勞動(dòng)關(guān)系,可以不簽訂勞動(dòng)合同。’該規(guī)定針對(duì)利用學(xué)習(xí)之余空閑時(shí)間打工補(bǔ)貼學(xué)費(fèi)、生活費(fèi)的在校學(xué)生,不視為就業(yè)和建立勞動(dòng)關(guān)系。但同時(shí),原勞動(dòng)部上述通知第4條,僅限制了公務(wù)員和比照實(shí)行公務(wù)員制度的事業(yè)組織和社會(huì)團(tuán)體的工作人員,以及農(nóng)村勞動(dòng)者、現(xiàn)役軍人和家庭保姆不適用勞動(dòng)法,并未明確將在校學(xué)生排除在外,學(xué)生身份并不當(dāng)然被限制其作為普通勞動(dòng)者與用工單位建立勞動(dòng)關(guān)系。事實(shí)上,在校學(xué)生身份確實(shí)關(guān)系到勞動(dòng)者工作時(shí)間是否受影響、能否順利完成所承擔(dān)的工作,但這并非審查確定勞動(dòng)者勞動(dòng)主體資格的依據(jù)。黃書(shū)舟入職時(shí)已本科畢業(yè),年滿(mǎn)16歲,身體健康,完全具備了勞動(dòng)法規(guī)定的勞動(dòng)行為能力和勞動(dòng)權(quán)利能力。黃書(shū)舟入職時(shí)雖已獲取研究生錄取通知書(shū),但其最終是否就讀研究生在入職時(shí)尚處于待定狀態(tài),且目前黃書(shū)舟因事故受傷嚴(yán)重未能就讀研究生,其在上海海事大學(xué)的學(xué)籍狀態(tài)僅為保留學(xué)籍。根據(jù)本案的情況,視黃書(shū)舟求職時(shí)為在校學(xué)生身份過(guò)于牽強(qiáng),不符合黃書(shū)舟的實(shí)際情況及勞動(dòng)法的立法目的。故本院認(rèn)定黃書(shū)舟2018年7月求職就業(yè)時(shí)身份并非在校學(xué)生,被告不能依據(jù)原勞動(dòng)部的上述規(guī)定而阻斷黃書(shū)舟作為勞動(dòng)者的主體資格。”(江蘇省南京市六合區(qū)人民法院(2018)蘇0116民初5423號(hào)民事判決書(shū))
綜合本文的分析可知,在讀的全日制研究生和在讀的全日制大學(xué)生、高中生一樣,通常還是適用原勞動(dòng)部《關(guān)于貫徹執(zhí)行<中華人民共和國(guó)勞動(dòng)法>若干問(wèn)題的意見(jiàn)》第12條的規(guī)定,認(rèn)定其與用人單位之間是不建立勞動(dòng)關(guān)系的。但是,如果該員工在就讀全日制研究生期間,其上班時(shí)間、工作內(nèi)容和勞動(dòng)強(qiáng)度等與本單位的其他正式員工基本一致,尤其是其在讀研以前就一直是在本單位就職的,那么,不排除存在認(rèn)定該員工與用人單位之間成立勞動(dòng)關(guān)系的可能性!
- end -
聲明:文中插圖來(lái)自互聯(lián)網(wǎng)。如涉侵權(quán),請(qǐng)聯(lián)系作者刪除!

 1359 人氣
1359 人氣